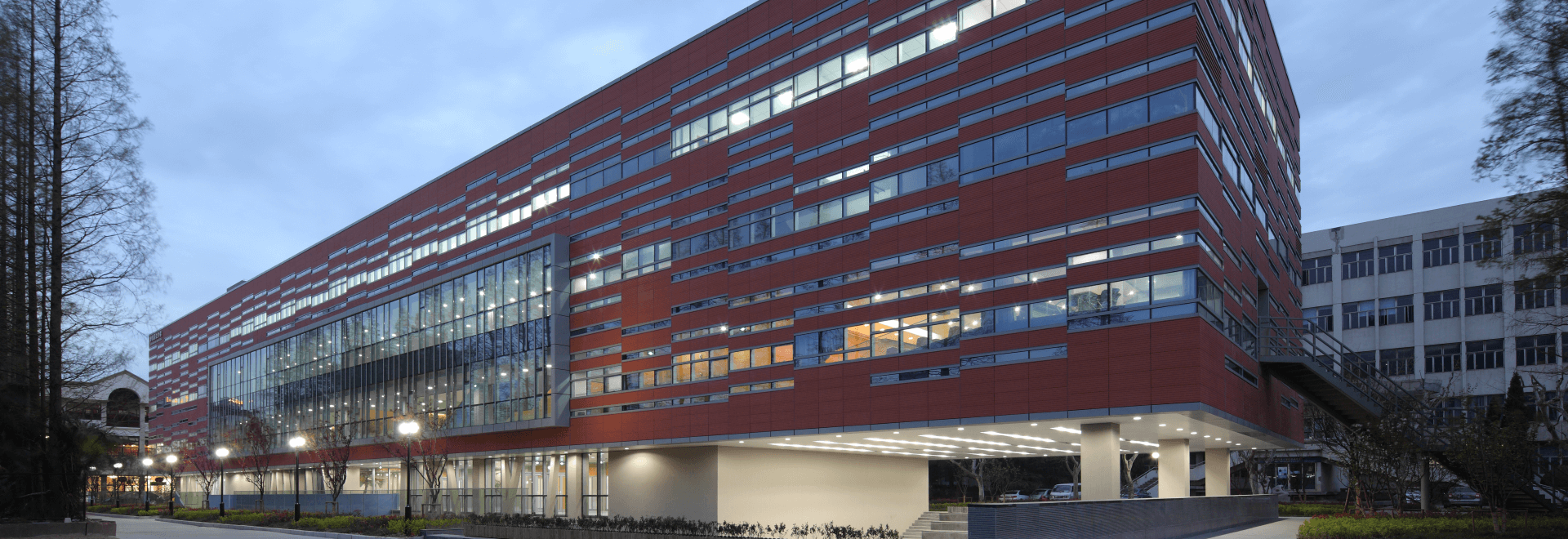

媒体聚焦
【凯原学者之声】范进学:人格权的民法规范体系化及其法治贡献 作者: 范进学 发布时间: 2020年08月25日
编者按:长期以来,凯原法学院学者关注国家改革和发展,关心民生,积极服务国家及政府,在国内外新闻媒体、期刊杂志等平台发表各类特约、评论文章,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范进学教授在《探索与争鸣》发表文章《人格权的民法规范体系化及其法治贡献》。他指出,中国《民法典》在保障平等主体的人身与财产权利上,除了注重保障公民的财产权,更注重保障公民的人格权,专设人格权编予以充分保护,这在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首开人格权编体例的法治保障先河;从规范体系化之视角观之,中国《民法典》实现了人格权的民法保护的体系化,使我国《宪法》关于“人格尊严”的基本权利规范得以通过民法规范而落实,从而构筑起了人格权保护的宪法与民法双重规范体系,在人类人格权法治保障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文章发表于2020年05期总第367期。
人格权的民法规范体系化及其法治贡献
纵观人类近现代数百年以来的民法典编纂史,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编纂的民法典对于人的权利保障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关于人格尊严权的立法体系化设计开创了人类人权法治保障史上的新篇章。
过往的民法典编纂最具典型性、标志性的模式是19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与19世纪末的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采取的是罗马法《法学阶梯》之人、物、诉讼三编之体例;德国民法典则采取罗马法《学说汇编》之总则、债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五编之体例,然而,无论是《法国民法典》抑或《德国民法典》,均是由它所赖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都受制于时代的局限而无法跳出时代之藩篱,它们无不镌刻着各自时代的烙印。《法国民法典》是18世纪鼓舞人心的启蒙思想的产物,深受自然法的自由与平等理念激情的侵淫,它彻底废除了封建领主的一切权利,确立了独立于宗教信条的个人自治与契约自由之理性精神,激荡着公民权利平等与自由理想,是法国“人权宣言”在法律形式上的具体体现;不过,《法国民法典》毕竟是反映18世纪思想的民法典,其功绩是秉承《人权宣言》关于“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的理性精神,在人格权保障史上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摈弃了罗马法以来人格身份不平等的制度,确立了人人平等的人权原则,而确立了“所有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的权利平等原则。其规定具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与政治意图,即以消除人格的身份等级差别为目的,实际上是“一部‘解放’人的法典”。因此,法国民法典虽初步实现了人的自由与平等的解放,却不可能完成对人的人格权利体系化保障,法国民法典之全面内容都是围绕个人之物权及其取得实现为核心。质言之,它是以物权之形式而实现人格权。
《德国民法典》诞生于风起云涌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其产生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然而它却未能呈现那个时代的精神与特色,正如谢怀拭教授所言:“对于德国而言,德国民法典只是完成了一个历史任务即统一德意志帝国的私法,未能把德国社会向前推进。德国比较法学家茨维克特与克茨对此评价指出,《德国民法典》具有的保守与守成的特点,这与长久以来在政治和经济上遭受打击的阶级的利益相一致;他们借用拉德布鲁赫的话说,《德国民法典》“与其说是20世纪的序曲,毋宁说是19世纪的尾声”;亦如奇特尔曼所言,它是“一个历史现实的审慎终结,而非一个新的未来的果敢开端”。此言不缪。《德国民法典》具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法律思想的烙印,“总则”作为首编确定了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平等以及契约当事人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思想,甚至第12条规定了姓名权之人格权,然而,整部《德国民法典》除了“总则”之外,其他三编债法、物权法、继承法也都是围绕“物”之权利而展开的,债权与物权是财产权之核心内容,继承则是财产移转而取得财产的一种方法,家庭法趋于保守并带有家长制的特征以及婚姻关系被设计为一种法律拟制的利益交换关系。
总之,《德国民法典》虽生效于20世纪之初,并对私法所有权神圣、意思自治及过错原则作出了一定限制,却没有充分体现个人权利尤其是人格权的保护,除了把人格置换为“权利能力”之法律主体资格,其他关于人格权的保障几乎缺失。严格意义上说,将人格置换为“权利能力”,是对人格权的贬低,“权利能力”表明的只是一种“法律主体”之资格权,而“法律主体”不仅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律拟制之“法人”,正如黑格尔所说:“人实质上不同于主体,因为主体只是人格的可能性,所有的生物一般来说都是主体”。因此,以“权利能力”作为法律主体资格取代“人格”,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在称谓上已经有些可鄙”。尹田教授也批评道:“《德国民法典》的人格在立法上被替换为‘权利能力’,成为一种纯粹的主体资格,不包含任何实质内容,将权利能力混同于人格,是有关人格、人格权的理论混乱发生的根源。”
无论如何,以上述两部法典所代表的西方传统民法,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把人的“财产”问题作为其保护的重点,而忽视了“人格”本身的保护。有学者对此指出:“近代民法以财产权利为中心, 主要体现为对外在财富的支配。这显然忽视了人的存在中的精神性的一面,人的内涵中的多样性被简单地物质化了”。也有学者评论说: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近代私法,民法上的人,与其说一个“享有私权,在权利上平等”的人,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财产权平等的人。德国法学家耶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民法的特征是重视财产权而轻视人,因为“谁侵害了他人的财产,就侵害了他人人格”。这种“无财产即无人格”的传统民法观念,被黑格尔表达得淋漓尽致,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针对罗马法把权利分为人格权、物权和诉权以及康德将权利分为物权、人格权以及物权性质的人格权的观点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认为这种划分是混乱的、乖缪而缺乏思辨思想,他指出:“惟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所以,人格权的本质是物权”;甚至断言:“物权就是人格本身的权利”。
“无物权即无人格”的观点,当然具有其合理性,梁慧星教授就明确指出:“一个毫无财产、一文不名的人,连生存都难以维持,能算是真正的人吗?……人只在享有财产权时,才能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也才有所谓人权和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尹田教授也指出:有关传统民法倡导“物文主义”(所谓“见物不见人”)的批评观点,将财产与人相分离, 忘记了民法所保护的财产都是为人所支配的物, 对财产的保护并非对物本身的保护 ,而是对人的保护。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将人的财产状况作为人格之享有的前提的观点,最大的问题是将人格与财产完全融合为一,这与人和人之外的事物不可能完全聚合的哲学原理相违背”。我们暂且抛开理论之争,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近代以来的民法传统虽通过财产权的保护而达到实现人格保护之目的,但确实没有将重点从保护财产转移到人格本身上来。
事实上,人类通过法律保护“人格权”的历史固然始于罗马法时代,但全面保障人格权的历史却始于二战之后。应该说,在二战之前,人格权的保护仅限于民法,近现代宪法产生之初,宪法典均未规定人格权的保护条款,如1791年的《法国宪法》与1787年的美国《宪法》皆未涉及人格保护内容;世界各国宪法文本在二战之前也几乎未将人格权保护载入宪法之中,如1920年的《奥地利宪法》、1937年的《爱尔兰宪法》、1922年的《拉脱维亚宪法》等等皆如此。二战结束后,人类鉴于法西斯国家政权对人权的肆无忌惮的侵害教训,在《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件中,将“人格尊严”保护写入其中,《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就规定:“人人生而平等,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宣布:“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因此,二战之后,各国在制定的宪法或修改后的宪法中,均将“人的尊严”或“人格尊严”保护载入宪法文本之中。德国宪法学者克里斯托夫·默勒斯认为:“宪法保障人的尊严,这种观念并非表达了永恒的普遍性,而是战后的典型产物。传统的宪法没有将人的尊严当做一项特有的基本权利。正是二战的恐怖催生了议会理事会,也促使《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阐明这项人权。”
1949年德国《基本法》将“人的尊严不可侵犯”载入宪法之后,之后各国在新制定的宪法中均把“人格尊严”纳入宪法之中。与此同时,受宪法上“人格尊严”的概念影响,民法上才开始出现“人格”+“尊严”即“人格尊严”概念。当法律人格与自然人格成为一回事之后,人格尊严与人的尊严、人性尊严几乎成为同义词。因而,关于人格的法律保护,的确是民法保护在先,并经历一个从身份不平等的人格权到平等的人格权、从特殊人格权到一般人格权、从民法人格权到宪法人格权到转变,同时宪法上人格尊严的保护对私法人格权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将人格权到人格尊严权的现代价值的转变。从此,人格尊严既受到民法的保护,也受到宪法上的保护。现代民法与宪法对于自然人的人格尊严的保护基本一致,都把人作为平等的人,尊重人的至高无上的内在理性价值,只是在防范的对象与救济的程序上有所不同:民法通过普通私法救济,防范来自于平等主体间的人格尊严的侵害;宪法则通过合宪性审查,防范来自国家公共权力的侵害。
我国《宪法》第38条确立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原则,然而,依照宪法第38条第2款之规定,“人格尊严”的宪法保护仅仅停留于“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义务行为模式之抽象保护上。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民法通则》第五章专设一节规定了“人身权”的保护,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及婚姻自主权纳入“人身权”范畴予以法律保护。
值得关注的是,《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保护,至少有两大不足:一是将人身权与人格权混同,把属于人格权的权利统统归于“人身权”之下;事实上,人身权与人格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前者是基于“人的身体”而享有的权利,如生命、健康、(人身)自由或(婚姻)自主等权利;后者是基于“人的至高无上的内在伦理价值”而享有的权利,如姓名、肖像、隐私、名誉、荣誉等。二是第101条将公民的人格尊严置于“名誉权”保护之下,未将宪法上确立的“人格尊严”基本权利作为基本人权对待,而是降格为“名誉权”之下的普通权利。《民法典》的修正了《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保护之弊端,除了在“总则”编中规定了一般人格权保护,还专设第四编——“人格权”编对具体人格权进行体系化的全面保护。这种人格权规范体系化的具体表现在于:
第一,“总则”第五章“民事权利”确立人格尊严法律保护的一般原则与基本内容体系,构筑了人格权保护法律规范体系:确立了“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的一般原则,界定了人格权的基本内涵即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以及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
第二,第四编“人格权”编,从一般人格权保护到具体人格权保护,构建起了法律规范体系:第4编第1章确立了一般人格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与侵权责任原则,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以及“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继承”的一般原则,同时规定了具体人格权受到侵害后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责任原则;第4编第2-6章就具体人格权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作出了具体规范保护。
应当说,中国民法典在保障平等主体的人身与财产权利上,除了注重保障公民的财产权,更注重保障公民的人格权,专设“人格权”编予以充分保护,这在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首开人格权编体例的法治保障先河;从规范体系化之视角观之,中国民法典实现了人格权的民法保护的体系化,从而使我国宪法关于“人格尊严”的基本权利规范得以通过民法规范而加以法律化并得以实施,从而构筑起了人格权的宪法与民法双重规范体系,从而在人类人格权法治保障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